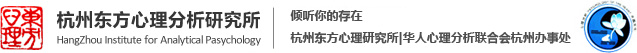心理分析
爱与丧失
Randy前几天在看一本书叫做A Grace Disguised How the Soul Grows Through Loss(《出人意外的祝福》)。书中讲述了杰瑞‧席哲的遭遇:一场出人意外、令人不解的车祸吞没了他一家人。在几秒钟之内,席哲的人生完全改观。一个酒醉的人驾驶的车辆迎头撞上席哲一家人乘坐的车辆,夺走了席哲的妻子、母亲、四岁大女儿的性命。在书中,席哲引领读者走过这场天翻地覆的事件,以及他对这场飞来横祸可能的意义所作的反思。一个人经过如此悲痛的损失,要如何生存。遭逢这样的巨变,该如何响应?本书英文版发行超过二十万册,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已经广泛用于小组、读书会、教会与会堂、收容所、神学院、医学院校、与大学课程,更被许多机构用作辅导那些遭受苦难之人的材料。
Randy觉得书中的一段特别值得一读,他想把这段内容作为高二上课的材料。可是手头只有英文版的,于是大原同志就在网上搜索中文版的书,可是如果买的话,一方面需要米,另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我就动手把那段译成了中文。译完以后,刘子亮还逐字阅读修改,对此,深感敬佩!有米的同志可以买一本书看一下,没米的同志就将就看一下Randy强烈推荐的这一段文字吧!o(∩_∩)o…哈哈
“一个团体并不会简单的自发形成,除非一些必要的条件具备时才行。甚至在有一些灾难性丧失的特别情况下,形成团体的条件也不是很充分。当遭受丧失的人们去寻找团体时,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会有意的做出一些选择去形成团体。
首先,这需要那些想为受难的朋友们营造一个团体的人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必须要愿意被其他人的丧失所改变,尽管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受到这些丧失的影响。好的安慰需要设身处地,需要力量的调整,有时还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提供安慰者一定要准备好去让设身处地的感受他人的痛苦并让痛苦转化安慰者。一旦做出这种决定,他们便已不是原来的自己。他们的世界会因为遭受痛苦的人的在场而被持久的改变。这会终结超然、控制感和便利性。这也不会再让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可爱的人,有很多正面的经历和可人环境的安全的地方。
从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那我一再听到相同的评论。“Jerry,你不知道你的经历多么严重的改变了我们”。他们提及这个悲剧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还有对意义的追求。他们被改变因为他们选择了卷入我的遭遇,并亲自承受我的痛苦。他们认为让我重回丧失之前的生活,仅仅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生活对我来说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来说同样如此。
事故发生时John还不到两岁。转瞬之间,他的股骨骨折,他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陷入极度悲伤之中。他的世界一片混乱,就像是他被丢入漩涡之中。大学里一些要好的朋友,Ron和Julie,他们每天都来医院看我。有一天他们问我,如果我工作的话打算让谁来照顾John。在我回答之前,Julie表示“为了长远发展”她愿意做John的代理妈妈。起初我是不同意这个想法的。但是她对我提出的每个问题都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作为一个母亲的解决方式。到现在已经有三年时间了,Julie白天的时候都在照看John,Ron也在帮忙。Julie参与了一些John的学前活动。当我无法带John去看医生时她会带John去医院。她让John融入她自己的家庭并给予他特别的关照。虽然她没有坚持要John叫她“妈妈”,但是在John的记忆里她已经是他的母亲了。她为John和我提供的无私的帮助的影响是无法衡量的。我相信John的快乐的性情和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Julie的巨大投入所带来的结果。
在事故发生后,来自大学和社区的一小组人决定每个星期和我会面提供支持,其实除了会面的其他时间我也经常看到他们。现在我们会面已有三年时间,这个小组已经不仅仅关注我作为一个悲伤的鳏夫的行为问题。我所任教的系里的同事用温情的关怀将我包围,至今为止,这个团体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紧密的一个团体。学院的其他同事鼓励我追求我的职业理想,尽管我用于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社区的朋友们也欢迎我加入我结婚时所归属的那个相同的社交圈子。
尤其是我的妹妹和妹夫Diane和Jack,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帮助我适应作为单亲父亲的生活,帮我建立新的家庭模式,并对未来做了规划。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花了许多时间通话,现在每周我们仍会通话两次或者三次。关于怎样抚养小孩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而且对于如何有效的管理家庭他们也提供了富有创意的方法。他们也和我一起去反思这个悲剧去发现它的意义,并依照我们的信条去理解这种丧失。此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最初和他们讨论时形成的。
我也经历了教会的鼎盛时期。当事故发生时我是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当时教会的成员即刻集结在我的周围。在短期内他们为我的家庭提供了食物和关怀,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和我一起去承受悲伤。这个丧失不仅仅是我们的。我的悲剧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它使集会中的许多人能够面对他们自己的种种丧失,其中的一些丧失可能已经埋藏或者被忽略了许多年之久。像其许多人一样,我目睹了教会的衰败。许多教会充满了伪君子、盲信者和淡漠的基督徒,对此大家已不再感到惊讶。然而,我发现我的教会团体依然富有同情心而且相互忠诚。我冒险给教会一个机会相信教会,教会也帮我和我的家庭度过难关。
在事故发生前我所归属的团体,换句话说,也是事故发生后我所归属的团体。当我哀伤、适应和改变的时候,这些团体为我提供了支持。他们保持忠诚的承诺让我不用再做另外一个适应:形成新的朋友圈子。他们的忠诚创造了一种关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这正是我在丧失之后体验忧伤并寻找新的生活时所需要的。我和这些朋友一起忧伤,这些朋友也让我感到忧伤,他们的存在让我想到了我所丧失的过去。但是这些朋友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所提供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也让我获得成长。他们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糟也变得更好,他们会勾起我对过去的回忆,但也有助于发现事故发生之后未来生活的挑战。
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也会有类似的影响。住在如此熟悉的地方,睡在原来的床上,看着房间的各种陈设——图片,相册,装饰,书籍,海报还有其余种种——所有这些都会唤醒对事故发生前生活的种种回忆,起初对我来说真的很难面对。我们整个的家庭让我想到Lynda和Diana Jane的离去。每次进门都会让我苦恼不已,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异常饥饿的人闻到了美食的馨香而却无法进食一样难受。但是同时这也提供了一个熟悉的环境,在这里我的孩子和我可以对四口之家建立一种新的认同感。我们家变成了一个进行试验和发现的实验室。它让我们感到悲伤,也在帮助我们成长。
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我决定留在家里过感恩节,不去拜访在州的另外一端的家庭。那年的冬天来得早些,这让我们都非常恋家。我也经历着很深的抑郁,在抑郁状态中我也陷入事故发生的第一个周年祭之中。这种抑郁也让我呆在家中的这四天所体验到的空虚感和疏离感更加恶化,四天时间长似数年。但是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接受了四口之家而且感到舒适,我们一起庆祝假期。我们胃口很好,拼命玩耍。尽管如此,这个长的周末就像一棵倾倒的树压在我的胸膛。有时我会被悲伤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也给我信心让我感到我们可以一起做得更好,即便是假期。这是我曾面对的最为艰难的假期,也是最为自由的假期。
团体经历也教会了我另外一课。想要安慰处于痛苦状态的人的安慰者需要做出决定去做这件事情,这还不够,而且需要得到安慰的人也必须决定接受安慰才行。他们的责任包括有勇气面对挫折,学习新的技能,努力争取互惠的友谊。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尽管他们正经历悲伤,体验心碎的感觉。我能学到这些大部分是因为我朋友们的温和鼓励,他们鼓励我在丧失中做出一些明智的选择。例如,Ron,Julie和我保持明晰的界限去防止我利用他们,同时也防止他们对我感到怨恨。Julie和我做出了一个时间表安排照看事宜,我雇了Monica作为兼职保姆。当Julie作为注册护士工作期间和Ron在学院工作期间,Monica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照看Julie的小儿子。
一个好朋友Susan志愿接送Catherine和David上学,并且这种极富价值的服务一做就是3年。但是我也尽快让自己能够适应轮流使用合伙使用的汽车,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也在教她的儿子足球。我尽己所能承担责任的期望迫使我去发展一些重要的管理技能,明智的安排我的时间以便我的家庭能够平稳运行。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时我会把鸡肉煮焦,会错过一些彩排,训练的时候会迟到,也会忘记送零食去学校。有一次我在一个50个大学生的班级上课时,忽然想起我忘记送Catherine去学校参加一个重要的音乐会。如果我们仅仅计划参加这个音乐会的话,那可能还会少些尴尬。但是Catherine在三个女孩的组合中要充当第一女高音的角色,那意味着她的缺席对整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导演而言。我惊慌的冲出教室,打电话给她的学校。但是为时已晚。我们错过了整个事件。当然事后我向导演道了歉,但是歉意对缺少Catherine的组合的表演者而言于事无补。
在事故发生后不久我意识到我还要承担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在团体中要做一个自己经历的解说者。朋友们想去倾听,想去同情。但是他们也想去学习,去反思苦难的一般性质,去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反思型的团体。我曾多次告诉我的这些朋友我是多么感激他们的同情关心,而对于我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从我的痛苦经历中发现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曾向我表示他们感激不尽。他们做好准备被改变,我也做好准备去履行我的责任。他们从未感到被操纵被利用,我也从未感到受恩于人,从未感到倍受压迫。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贡献,我们每个人也在获得。
结果就是爱。我们学着更深入的去爱。对我来说,虽然不是独有的真实,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真实。起初对于冒险去爱我犹豫不决。这是我的一种保护性反射,这会使我想疏离每个人,甚至是我的家人。我的经历教会我丧失会让人退回到一种几乎完全心碎并且极易受伤的状态。我不是仅仅感到切肤之痛,我整个人就是疼痛本身。结果我经常发现我自己总是在接受爱和友谊。然而,最终我不得不决定去重新做一个对团体有所贡献的成员,不仅接受爱,而且给予爱。
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从来都不是。人们对重新给予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他们害怕会重新丧失,这是人之常情。心智正常的人有谁会想要再次经历这种痛苦呢?如果有如此风险,那么给予爱还值不值得?甚至当你知道还会有其他丧失会接踵而来,你在丧失之后还会有爱的可能性吗?我曾无数次的想到如果我再失去另外一个小孩的话,那对我而言是多么致命的一个打击,尤其是现在我对他们付出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之下。我被那种可能性吓坏了。但是我也无法想象我不去爱他们,那对我来说比失去他们更为令人厌恶。
因而更多丧失的风险造成了一个困境。选择继续去爱的问题是做出选择去爱意味着活在继续丧失的威胁之下。但是选择不去爱的问题是远离爱意味着危及心灵的生活,因为心灵只有在爱的滋养下才能茁壮成长。心灵健全的人选择去爱,心灵孱弱的人选择不爱。如果人们想要他们的心灵通过丧失——不论何种丧失——成长,他们一定最终决定去爱,甚至比他们以前爱的更为强烈。他们必须用更为充沛的能量和承诺拥抱爱,以此来回应丧失。
不论怎样,那是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立即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他们是如此的需要一个父亲在悲剧发生后去爱他们。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发现我作为一个父亲如何照看我的孩子将会决定他们将来如何看待和对待这场悲剧。事故发生后大概6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不同寻常的电话,她想和我谈谈她母亲的过世这个事情。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交谈。我甚至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她说在她10岁的时候她母亲过世了。她20岁的时候开始找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时断时续持续了6年的治疗。我对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和恐惧。我想如果她仅仅是给我一个如此令人沮丧的信息,为何她会打电话给我。但是接着她就解释为何去寻求心理治疗。不是像我假设的那样是由于她母亲的过世。她寻求心理治疗是要处理父亲的丧失,虽然父亲还在世。她说,她父亲在自己的妻子过世以后,就开始疏离自己的孩子。虽然他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但是在情感上,父亲变得遥不可及。她父亲对丧失的这种反应对她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丧失,因为她失去了一个亲人,尽管父亲仍然活着而且有能力爱她,但是他选择不去爱她。
那个电话对我而言是个很好的礼物。它提醒我作为三个受到创伤感到困惑的孩子的父亲,我所拥有的机遇和权利。我不想让一个丧失——他们母亲的过世——导致另外一个丧失,同样是不可忍受的丧失,那就是徒有空壳毫无生气的一个父亲。所发生的事故已令人难以承受,我不能在雪上加霜:疏离他们,剥夺他们所需要的父爱。我想通过良好的表现来超越邪恶。
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我意识到尤其在遭遇丧失之后,会存在一种不详的爱。如果丧失会增强我们爱的能力,那么这种增强了的爱的能力在重新遭受打击之后会令我们感到更大的伤害。对此困境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选择疏离人们保护自己会让自己的心灵萎缩,选择去爱甚至比以前更强烈的去爱会让我们重新遭遇痛苦,因为选择去爱需要有勇气去忍受悲伤。我们知道人的一生不会只有一次丧失。所以我们害怕令人担忧的丧失是自然的。但是更大的丧失不是遭遇另外的丧失本身,而是拒绝去爱,因为拒绝去爱会导致灵魂的死亡。
当我们心碎的时候,我们要有巨大的勇气才会选择去爱。但是我在想当爱超越了心碎之后才会变得更为真实。心碎的感觉让我们去找寻我们自身之外的爱的根源。这源自一种神性,这种神性的根本性质就是爱。把心碎的感觉和爱放在一起看似矛盾,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同根同源的。
过去的三年时间,我和一些人有着很愉快的会面。当他们从痛苦的体验中走出来时,那是极富意义的事情。一个学院的朋友看起来非常无助,他的妻子忍受了一年的乳房癌的治疗。我的遭遇和他对妻子的关心使我们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院的一个员工最近检查出患了癌症。再次,我们的交谈有了更多的共鸣。最近我和一个我们教会的女士聊天,由于输了感染病毒的血而患了艾滋病。她的几个孩子还小,她很担心他们,她爱她的丈夫也很能为他着想。我们讨论了我们处境的独特性。我们在探寻意义,试图去领会我们的遭遇。倾听她的故事并分享我的体验,让我能够继续向前。
自从那次事故之后,我对人们充满感激之情,尽管我从未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无力感和无能感。我的遭遇把心碎的感觉和爱结合在一起。心碎的感觉驱使我去爱,并且我发现了在我自身无法找到的爱的根源。我在团体中找到了它,在神性中找到了它,这种神性为像我一样心碎的人创造和维持了这个团体。”
Randy觉得书中的一段特别值得一读,他想把这段内容作为高二上课的材料。可是手头只有英文版的,于是大原同志就在网上搜索中文版的书,可是如果买的话,一方面需要米,另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我就动手把那段译成了中文。译完以后,刘子亮还逐字阅读修改,对此,深感敬佩!有米的同志可以买一本书看一下,没米的同志就将就看一下Randy强烈推荐的这一段文字吧!o(∩_∩)o…哈哈
“一个团体并不会简单的自发形成,除非一些必要的条件具备时才行。甚至在有一些灾难性丧失的特别情况下,形成团体的条件也不是很充分。当遭受丧失的人们去寻找团体时,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会有意的做出一些选择去形成团体。
首先,这需要那些想为受难的朋友们营造一个团体的人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必须要愿意被其他人的丧失所改变,尽管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受到这些丧失的影响。好的安慰需要设身处地,需要力量的调整,有时还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提供安慰者一定要准备好去让设身处地的感受他人的痛苦并让痛苦转化安慰者。一旦做出这种决定,他们便已不是原来的自己。他们的世界会因为遭受痛苦的人的在场而被持久的改变。这会终结超然、控制感和便利性。这也不会再让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可爱的人,有很多正面的经历和可人环境的安全的地方。
从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那我一再听到相同的评论。“Jerry,你不知道你的经历多么严重的改变了我们”。他们提及这个悲剧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还有对意义的追求。他们被改变因为他们选择了卷入我的遭遇,并亲自承受我的痛苦。他们认为让我重回丧失之前的生活,仅仅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生活对我来说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来说同样如此。
事故发生时John还不到两岁。转瞬之间,他的股骨骨折,他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陷入极度悲伤之中。他的世界一片混乱,就像是他被丢入漩涡之中。大学里一些要好的朋友,Ron和Julie,他们每天都来医院看我。有一天他们问我,如果我工作的话打算让谁来照顾John。在我回答之前,Julie表示“为了长远发展”她愿意做John的代理妈妈。起初我是不同意这个想法的。但是她对我提出的每个问题都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作为一个母亲的解决方式。到现在已经有三年时间了,Julie白天的时候都在照看John,Ron也在帮忙。Julie参与了一些John的学前活动。当我无法带John去看医生时她会带John去医院。她让John融入她自己的家庭并给予他特别的关照。虽然她没有坚持要John叫她“妈妈”,但是在John的记忆里她已经是他的母亲了。她为John和我提供的无私的帮助的影响是无法衡量的。我相信John的快乐的性情和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Julie的巨大投入所带来的结果。
在事故发生后,来自大学和社区的一小组人决定每个星期和我会面提供支持,其实除了会面的其他时间我也经常看到他们。现在我们会面已有三年时间,这个小组已经不仅仅关注我作为一个悲伤的鳏夫的行为问题。我所任教的系里的同事用温情的关怀将我包围,至今为止,这个团体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紧密的一个团体。学院的其他同事鼓励我追求我的职业理想,尽管我用于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社区的朋友们也欢迎我加入我结婚时所归属的那个相同的社交圈子。
尤其是我的妹妹和妹夫Diane和Jack,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帮助我适应作为单亲父亲的生活,帮我建立新的家庭模式,并对未来做了规划。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花了许多时间通话,现在每周我们仍会通话两次或者三次。关于怎样抚养小孩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而且对于如何有效的管理家庭他们也提供了富有创意的方法。他们也和我一起去反思这个悲剧去发现它的意义,并依照我们的信条去理解这种丧失。此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最初和他们讨论时形成的。
我也经历了教会的鼎盛时期。当事故发生时我是第一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当时教会的成员即刻集结在我的周围。在短期内他们为我的家庭提供了食物和关怀,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和我一起去承受悲伤。这个丧失不仅仅是我们的。我的悲剧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它使集会中的许多人能够面对他们自己的种种丧失,其中的一些丧失可能已经埋藏或者被忽略了许多年之久。像其许多人一样,我目睹了教会的衰败。许多教会充满了伪君子、盲信者和淡漠的基督徒,对此大家已不再感到惊讶。然而,我发现我的教会团体依然富有同情心而且相互忠诚。我冒险给教会一个机会相信教会,教会也帮我和我的家庭度过难关。
在事故发生前我所归属的团体,换句话说,也是事故发生后我所归属的团体。当我哀伤、适应和改变的时候,这些团体为我提供了支持。他们保持忠诚的承诺让我不用再做另外一个适应:形成新的朋友圈子。他们的忠诚创造了一种关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这正是我在丧失之后体验忧伤并寻找新的生活时所需要的。我和这些朋友一起忧伤,这些朋友也让我感到忧伤,他们的存在让我想到了我所丧失的过去。但是这些朋友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所提供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也让我获得成长。他们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糟也变得更好,他们会勾起我对过去的回忆,但也有助于发现事故发生之后未来生活的挑战。
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也会有类似的影响。住在如此熟悉的地方,睡在原来的床上,看着房间的各种陈设——图片,相册,装饰,书籍,海报还有其余种种——所有这些都会唤醒对事故发生前生活的种种回忆,起初对我来说真的很难面对。我们整个的家庭让我想到Lynda和Diana Jane的离去。每次进门都会让我苦恼不已,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异常饥饿的人闻到了美食的馨香而却无法进食一样难受。但是同时这也提供了一个熟悉的环境,在这里我的孩子和我可以对四口之家建立一种新的认同感。我们家变成了一个进行试验和发现的实验室。它让我们感到悲伤,也在帮助我们成长。
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我决定留在家里过感恩节,不去拜访在州的另外一端的家庭。那年的冬天来得早些,这让我们都非常恋家。我也经历着很深的抑郁,在抑郁状态中我也陷入事故发生的第一个周年祭之中。这种抑郁也让我呆在家中的这四天所体验到的空虚感和疏离感更加恶化,四天时间长似数年。但是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们接受了四口之家而且感到舒适,我们一起庆祝假期。我们胃口很好,拼命玩耍。尽管如此,这个长的周末就像一棵倾倒的树压在我的胸膛。有时我会被悲伤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也给我信心让我感到我们可以一起做得更好,即便是假期。这是我曾面对的最为艰难的假期,也是最为自由的假期。
团体经历也教会了我另外一课。想要安慰处于痛苦状态的人的安慰者需要做出决定去做这件事情,这还不够,而且需要得到安慰的人也必须决定接受安慰才行。他们的责任包括有勇气面对挫折,学习新的技能,努力争取互惠的友谊。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尽管他们正经历悲伤,体验心碎的感觉。我能学到这些大部分是因为我朋友们的温和鼓励,他们鼓励我在丧失中做出一些明智的选择。例如,Ron,Julie和我保持明晰的界限去防止我利用他们,同时也防止他们对我感到怨恨。Julie和我做出了一个时间表安排照看事宜,我雇了Monica作为兼职保姆。当Julie作为注册护士工作期间和Ron在学院工作期间,Monica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照看Julie的小儿子。
一个好朋友Susan志愿接送Catherine和David上学,并且这种极富价值的服务一做就是3年。但是我也尽快让自己能够适应轮流使用合伙使用的汽车,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也在教她的儿子足球。我尽己所能承担责任的期望迫使我去发展一些重要的管理技能,明智的安排我的时间以便我的家庭能够平稳运行。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时我会把鸡肉煮焦,会错过一些彩排,训练的时候会迟到,也会忘记送零食去学校。有一次我在一个50个大学生的班级上课时,忽然想起我忘记送Catherine去学校参加一个重要的音乐会。如果我们仅仅计划参加这个音乐会的话,那可能还会少些尴尬。但是Catherine在三个女孩的组合中要充当第一女高音的角色,那意味着她的缺席对整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导演而言。我惊慌的冲出教室,打电话给她的学校。但是为时已晚。我们错过了整个事件。当然事后我向导演道了歉,但是歉意对缺少Catherine的组合的表演者而言于事无补。
在事故发生后不久我意识到我还要承担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我在团体中要做一个自己经历的解说者。朋友们想去倾听,想去同情。但是他们也想去学习,去反思苦难的一般性质,去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反思型的团体。我曾多次告诉我的这些朋友我是多么感激他们的同情关心,而对于我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从我的痛苦经历中发现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曾向我表示他们感激不尽。他们做好准备被改变,我也做好准备去履行我的责任。他们从未感到被操纵被利用,我也从未感到受恩于人,从未感到倍受压迫。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贡献,我们每个人也在获得。
结果就是爱。我们学着更深入的去爱。对我来说,虽然不是独有的真实,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真实。起初对于冒险去爱我犹豫不决。这是我的一种保护性反射,这会使我想疏离每个人,甚至是我的家人。我的经历教会我丧失会让人退回到一种几乎完全心碎并且极易受伤的状态。我不是仅仅感到切肤之痛,我整个人就是疼痛本身。结果我经常发现我自己总是在接受爱和友谊。然而,最终我不得不决定去重新做一个对团体有所贡献的成员,不仅接受爱,而且给予爱。
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从来都不是。人们对重新给予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他们害怕会重新丧失,这是人之常情。心智正常的人有谁会想要再次经历这种痛苦呢?如果有如此风险,那么给予爱还值不值得?甚至当你知道还会有其他丧失会接踵而来,你在丧失之后还会有爱的可能性吗?我曾无数次的想到如果我再失去另外一个小孩的话,那对我而言是多么致命的一个打击,尤其是现在我对他们付出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之下。我被那种可能性吓坏了。但是我也无法想象我不去爱他们,那对我来说比失去他们更为令人厌恶。
因而更多丧失的风险造成了一个困境。选择继续去爱的问题是做出选择去爱意味着活在继续丧失的威胁之下。但是选择不去爱的问题是远离爱意味着危及心灵的生活,因为心灵只有在爱的滋养下才能茁壮成长。心灵健全的人选择去爱,心灵孱弱的人选择不爱。如果人们想要他们的心灵通过丧失——不论何种丧失——成长,他们一定最终决定去爱,甚至比他们以前爱的更为强烈。他们必须用更为充沛的能量和承诺拥抱爱,以此来回应丧失。
不论怎样,那是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立即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他们是如此的需要一个父亲在悲剧发生后去爱他们。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发现我作为一个父亲如何照看我的孩子将会决定他们将来如何看待和对待这场悲剧。事故发生后大概6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不同寻常的电话,她想和我谈谈她母亲的过世这个事情。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交谈。我甚至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她说在她10岁的时候她母亲过世了。她20岁的时候开始找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时断时续持续了6年的治疗。我对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和恐惧。我想如果她仅仅是给我一个如此令人沮丧的信息,为何她会打电话给我。但是接着她就解释为何去寻求心理治疗。不是像我假设的那样是由于她母亲的过世。她寻求心理治疗是要处理父亲的丧失,虽然父亲还在世。她说,她父亲在自己的妻子过世以后,就开始疏离自己的孩子。虽然他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但是在情感上,父亲变得遥不可及。她父亲对丧失的这种反应对她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丧失,因为她失去了一个亲人,尽管父亲仍然活着而且有能力爱她,但是他选择不去爱她。
那个电话对我而言是个很好的礼物。它提醒我作为三个受到创伤感到困惑的孩子的父亲,我所拥有的机遇和权利。我不想让一个丧失——他们母亲的过世——导致另外一个丧失,同样是不可忍受的丧失,那就是徒有空壳毫无生气的一个父亲。所发生的事故已令人难以承受,我不能在雪上加霜:疏离他们,剥夺他们所需要的父爱。我想通过良好的表现来超越邪恶。
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我意识到尤其在遭遇丧失之后,会存在一种不详的爱。如果丧失会增强我们爱的能力,那么这种增强了的爱的能力在重新遭受打击之后会令我们感到更大的伤害。对此困境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选择疏离人们保护自己会让自己的心灵萎缩,选择去爱甚至比以前更强烈的去爱会让我们重新遭遇痛苦,因为选择去爱需要有勇气去忍受悲伤。我们知道人的一生不会只有一次丧失。所以我们害怕令人担忧的丧失是自然的。但是更大的丧失不是遭遇另外的丧失本身,而是拒绝去爱,因为拒绝去爱会导致灵魂的死亡。
当我们心碎的时候,我们要有巨大的勇气才会选择去爱。但是我在想当爱超越了心碎之后才会变得更为真实。心碎的感觉让我们去找寻我们自身之外的爱的根源。这源自一种神性,这种神性的根本性质就是爱。把心碎的感觉和爱放在一起看似矛盾,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同根同源的。
过去的三年时间,我和一些人有着很愉快的会面。当他们从痛苦的体验中走出来时,那是极富意义的事情。一个学院的朋友看起来非常无助,他的妻子忍受了一年的乳房癌的治疗。我的遭遇和他对妻子的关心使我们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院的一个员工最近检查出患了癌症。再次,我们的交谈有了更多的共鸣。最近我和一个我们教会的女士聊天,由于输了感染病毒的血而患了艾滋病。她的几个孩子还小,她很担心他们,她爱她的丈夫也很能为他着想。我们讨论了我们处境的独特性。我们在探寻意义,试图去领会我们的遭遇。倾听她的故事并分享我的体验,让我能够继续向前。
自从那次事故之后,我对人们充满感激之情,尽管我从未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无力感和无能感。我的遭遇把心碎的感觉和爱结合在一起。心碎的感觉驱使我去爱,并且我发现了在我自身无法找到的爱的根源。我在团体中找到了它,在神性中找到了它,这种神性为像我一样心碎的人创造和维持了这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