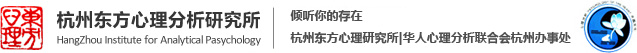心理分析
荣格是谁?
申荷永
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的时候,世界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与阴影之中,荣格也在他的无意识领域探索着。在以后的20多年中,世界格局以及心理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的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战争考验了心理学的应用,也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由于恢复战争创伤的需要,精神分析更加受到重视;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呈现出其潜在的意义,荣格与其分析心理学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卡尔·荣格印象
若是从照片上来看,年轻时的荣格与老年的荣格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一是强硬与果敢气质的表现,一是神秘而富有智慧的感觉。实际上,强硬、神秘与智慧,这都是人们对于荣格的基本印象。
(一)石头中的情结
荣格有着深深的“石头情结”,他的心理分析也与“石头”有着不解的渊源。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曾有这样一段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描述:“‘我坐在下面的石头上,’但是这石头也可以说‘我’并且想:‘我躺在这斜坡上,他坐在我上面。’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呢?还是被那个人坐着的石头?’这样的想法总是困惑着我,于是我会站起来,想分清楚到底谁是谁。”[1]
荣格回忆说,这个问题长久而得不到答案,一种奇怪的思虑一直伴随着自己。“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个小时,被它所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逗引得晕头转向。”
那时他还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30年过后,荣格已经成家立业,功成名就。他站在那道斜坡上,再看童年时曾坐着幻想的石头,他说“突然我又变成那个曾经点一堆意义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灵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2]
就是这么一块普通的石头,使荣格获得了深远的思想。后来,荣格知道这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自然的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于是,像许多西方的学者一样,荣格对 “蝴蝶道者”的庄子十分神往。坐在石头上的荣格,幻想着“自我”与“石头”的互换,极为类似庄周与蝴蝶的“物化”体验。
荣格深信,这石头与他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甚至把石头作为他“第二人格”的象征。荣格在其自传中说:“每当(他)想到(他)是石头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舒适感……”“石头安定而实在,沉默不语,千万年来保持着如此的禀性。”荣格曾深有感触地说:“(他)所具有的另外一种存在(其第二人格),就是那永恒而不朽的石头。” 于是,荣格与“石头”有着不解的渊源。他曾经说这种关联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无尽神秘,心灵的具体表现。”[1]
“石头情结”伴随着荣格的一生。他用石头建筑了他的波林根塔楼,他在隐居中感悟智慧。而他留在波林根的石刻,就像波林根一样著名,尤其是那“三面刻石”,几乎就是荣格心理分析的象征。
在石刻的正面,面向塔楼的东面,荣格自己在石头的纹路中“看到”了一个“圆圈”,像是一只大眼睛在看着他。于是他就刻了这么一个圆圈,并且在中间还刻了一个小矮人,包含着“你在别人眼睛的瞳孔里所看到的你”的意思。这“小矮人”身穿钟形斗篷,手持一盏灯,俨然像一位指路人。荣格用拉丁文刻了这么一段话:
“时光是个孩子…… 像孩子那样在玩耍……玩着棋盘游戏……孩子的王国与天下。这就是泰雷斯富鲁斯(Telesphoros)[1],他在这宇宙的黑暗处徜徉,像透过夜空的星星那样闪闪发光。他指引着通往太阳和梦国之门的道路。”
在石刻的第三面,也就是朝向湖的那一面,荣格说是他让石头自己“说话”的,石头“说”了什么,他就刻上什么:“我是一个孤儿,孤独一人。然而我浪迹着天涯。我是一个人,但却又与自己相反。我同时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为我曾像鱼一样在深水中被捞起,或像是一块从天而降的白色的石头。我游荡在树林山间,但又隐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也是必死的凡人,但我又不受生命轮回的影响。”
荣格说,“这石头伫立在塔楼的外面,像是对这塔楼的注解。它也正是那居住者的心声,只是尚不为他人所理解。”荣格也曾问那些好奇的人:“你知道我想在这石头的背面刻什么吗?”石头中仍然包含着许多秘密。荣格说这石头使他想起梅林,想起梅林从森林深处发出的呼喊。于是,“梅林的喊叫声”(Le cri de Merlin)[2] 就是那未刻上去的文字。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喊叫声,但是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这叫喊声。
这是荣格的石头情结,也是他要在其心理学中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其分析心理学所包含的神秘色彩。
(二)神秘中的探索
记得在一次关于荣格心理学的讲座中,主持人想着让大家谈一下各自对荣格的印像,类似于自由联想或词语联想的练习。参加者80余人,最集中的回答便是“神秘”。终日坐在石头上幻想的孩子,是显得神秘的,或至少伴随着某种神秘的气氛。而这种终日的神秘向往,导致了荣格童年的另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
荣格在其自传中记述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荣格在其上学用的尺子上,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礼服,戴着高帽子,脚登一双亮闪闪的黑轮靴子。”荣格用墨水把它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同时,荣格还在铅笔盒里给这小矮人做了一张小床,用一点儿羊毛给它做了件大衣。同时,荣格去莱茵河边给这小矮人找来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也放进了铅笔盒。
荣格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神秘。他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的阁楼,藏在一根大梁上,他为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我经常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注视、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语言。”
荣格说,“心中藏有秘密,对我的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这种藏有秘密的孩子的神秘气氛,也就不仅仅是荣格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荣格成长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从他读大学开始,尽管读的是医学,荣格对于心灵的神秘感再次浮现。即使是阅读一些有关心灵感应或超心理学的书籍与资料,在当时绝大部分的学者眼中那纯属无稽之谈,荣格却总是倾向于接受与相信其真实性。荣格在其自传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和极为吸引人的。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点什么关系吗?”[1]
在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记录了这样两个事件。其一,在1898年暑假的一天,荣格正坐在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饭厅的门敞开着,饭厅里有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是荣格祖母的嫁妆,已有七十多年了。荣格的母亲坐在里面织毛线。突然间,砰地一声作响。荣格跳起来快步冲进房间,只见他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直盯着那张桌子。响声正是那胡桃木餐桌发出的,桌面上显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缝。荣格的妈妈深沉地说:“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
荣格的神秘感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母亲。他曾回忆到,在他小的时候,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和神秘。而这古怪与神秘的气氛,也带给荣格很多古怪而神秘的梦。
在胡桃木餐桌裂开的两周后,荣格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全家人正处在激动不安的状态,原来又发生了同样的惊响,但不再是胡桃木餐桌的裂开,而是放在餐具柜里的一把餐刀,断裂成三节。在那以后,荣格开始参加他亲戚家里举行的“降神会”,几个星期以后,他听说几个亲戚在搞桌子转动的事:他们当中有一个降神者,一个15岁或16岁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他见见这个降神者,据说这个姑娘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想到了在他屋里的那种古怪的现象,于是他便猜想,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降神者有联系。于是,他便开始列席“降神会”。
就在这“降神会”里,荣格发现了他表妹海琳(Helene Preiswerk)的特异能力,并开始以她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1902)。而他从巴塞尔大学毕业之后,提交给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的就职论文,仍然是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这种对“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和“特异心灵现象”的研究兴趣,一直伴随着荣格的整个一生。荣格在面对无意识的探索过程中“遇到”““斐乐蒙””(Philemon),在”“斐乐蒙””的启发下撰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都充满着这种神秘的色彩。就是到了晚年,荣格仍然对“飞碟现象”倍感兴趣。
但是,这种“神秘”或“神秘的色彩”,在荣格的生涯中得到了积极与有效的发挥,尽管保留着其消极和迷信的成分。当这种神秘促进探索的时候,总是积极的,那也正是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当这种神秘融入智慧的时候,更成为一种精神的升华。
(三)隐居中的智慧
荣格曾自称是一个孤独者,尤其是尼采意义上的孤独者。他也曾在晚年隐居他的波林根,自己在苏黎世的郊外所建造的塔楼。隐居是显得神秘的,但隐居者与孤独者也往往是智者。隐居与孤独培育着智慧。
荣格在1902年买下了位于苏黎世湖尽头的波林根的一片土地。那里本来是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嘉尔修道院。1923年荣格的母亲去世后,他着手建造塔楼的最初结构,后来有几次扩建,历时12年完成了波林根的塔楼。1947年荣格72岁时,正式退隐波林根。
在今天看来,波林根是湖光山色且带有田园色彩十分优美的地方,但是,在荣格隐居那里的时候,实际上直到现在,塔楼里没有任何通电的设备,没有电灯电话,没有空调与冰箱。荣格自己曾这样来描述他在那里的生活:
“这里没有电力设施,天冷的时候我靠向火炉取暖。傍晚时分,我燃起油灯。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从井中打水;我劈柴用来烧饭。这些简单的工作使人变得简单;但是变得简单又是何等的艰难!”[1]
简单接近自然,简单能够使人单纯。荣格说,“在波林根,我处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他在那里有自己的一间“沉思室”,退隐中更为隐秘的地方。荣格说每当他进入那房间,就会感到一种轻松与自然。“思绪不断地涌现,回荡着多少个世纪的往事,也预现着那遥远的未来。在这里,那创造的痛苦得以缓解,创造与游戏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2] 于是,荣格感触地说,“住在波林根的这座塔楼里,一个人便仿佛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纪似的。”
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是这样描述他的波林根以及他在波林根的感受的:
我时常觉得我自己也伸展向那无际的旷野以及周围一切存在的内部。我觉得我是生活在每一棵树中,每一朵浪花的耀动之间,生活于云雾与动物的穿梭,以及季节的变化之中。这塔中的一切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注入了其自己的特色,而每一特色也都与我息息相关。在这里,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以及和我的历史,这里是心灵特有世界的无限的王国。
在汉娜撰写的荣格传记《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中,她把1945—1952称为荣格的“丰收”季节。荣格曾于1944年生了一场重病,严重的心脏血栓,多亏一位H医生,才使得他死里逃生。此后荣格修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汉娜写道:“荣格便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在此期间,他最重要的几部书写成了。”[3] 而荣格自己也曾十分明确地回忆说:
经过那场疾病之后,一个丰富的工作阶段开始了。我的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那时候完成的。我所获得的灵感,或者是对于所有问题的本质性洞察,使我获得勇气来表达新的思想与理论。我不再试图阐述自己的意见,而是让自己沉浸于新的思想之中。于是,问题一个接一个自行向我展现并且获得其表达的形式。[4]
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的最后一页,荣格援引老子的话:“众人皆清,惟我独懵。”作为其自传的最后总结。荣格说,老子所表达的正是他在老年所感受到的。荣格称老子就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他具有超越的智慧,可以看到以及真切地体验到价值与无价值。受老子的影响,荣格在其晚年渴望着回归其本来的存在,回归那永恒的未知的意义。荣格说:“智慧老人的原型所洞察的是永恒的真理……我对于我自己越是感到不确定,越是有一种内在生发的,与所有的存在均有联系的感觉。事实上,似乎那长期以来使我脱离于世界的疏离感,已经转化为我内在的世界,同时展现给我一种意外而新颖的我自己。”[5]
于是,孤独与隐居,体现为荣格的智慧。荣格去世前曾有这样两个梦境。一是关于波林根的:在梦中,“他看见了‘另一个波林根’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一个声音对他说,现在已经完工了,可以准备住人了。”另外一个梦,也是汉娜记在其《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中的,就在荣格去世前的某个晚上,荣格在梦中看见一块大的圆石头,上面刻着:“这是你的完整性和同一性的标记。”[1] 于是,石头、神秘与智慧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荣格,也是荣格留下来的印象。
[1] 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0页。
[2] 同上。
[1] 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42页,第68页。
[1] 泰雷斯富鲁斯(Telesphoros):传说中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或Asklepios)的儿子,健康女神海吉尔(Hygieia)和治愈女神潘娜希(Panacea)的兄弟。
[2] 梅林:传说是阿瑟王时代的诗人和巫师,据说曾被女巫关入岩石中,后被魔法困在荆棘丛中,从此便一直深睡,但有时人们却可以听见他的叫喊。
荣格对“梅林”的注解:梅林代表了中世纪的无意识想创造一个与巴斯法尔(Parsifal)对等的人物的意图。巴斯法尔是个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这个魔鬼和一个纯洁的处女所生的儿子则是前者的阴暗的兄弟。在12世纪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仍然没有存在着什么可以据之以了解他那固有的含义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结,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声”一说,而这喊叫声在他死后仍然从森林里传出来。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喊叫声意味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而活着。他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他仍然在到处走动着。可以这样说,梅林的秘密由炼丹术而流传下来了,而且主要是通过墨丘利乌斯(Mercurius)这个人物才流传下来的。因此,梅林这个人物是在我那无意识心理学里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要与无意识密切地一起生活可太难做到了。我反复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这样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的难。
[1] 荣格:《回忆•梦•思考》,刘国彬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1] 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25—226页。
[2] 同上。
[3] 芭芭拉·汉娜:《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4] 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97页。
[5] 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359页。
[1] 芭芭拉·汉娜:《荣格的生活与工作》,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53页。